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也影响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文与历史学者研究者纷纷投入到对该领域的探讨中。2023年12月16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跨文化科技交流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史国际前沿学术论文研读会”第9期在线上召开。本期研读会以“理解气候:文化与历史的视角”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博士生博尔琛、南开大学博士生郭庆以及清华大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讲师仇振武进行领读。与谈嘉宾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奥斯陆大学客座研究员敖友华(erling agøy),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乔瑜,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特别研究助理孙萌萌。
博尔琛分享了mark carey教授的文章“climate and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ical climat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historiography”。文章探讨了气候历史研究的四个重要领域,分别是气候重建、社会影响与响应、气候知识的使用和滥用、气候文化的建构与感知。
气候重建是通过自然档案或社会档案来重现过去的气候信息的一种研究方法。来自气候史、历史气候学、以及古气候学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其中,使其成为一个跨学科交叉领域。气候重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为研究气候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基础。社会影响与响应则是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类社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它可以揭示气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气候因此成为与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力量并存的众多变量之一。尽管如此,学者们有时候也批评这类研究滑向了“气候决定论”,因此研究气候知识的使用和滥用就变得极有必要。这些研究可以揭示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气候科学的知识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作者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气候知识是如何被用来为殖民主义等不平等的制度和现象辩护或反抗的,以及西方气候知识如何与本土生态知识(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相结合。当然,气候知识的生成与人们对气候文化的建构与感知密不可分。这是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的文化表达、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展示气候与文化的相互塑造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作者认为对气候变化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气候史研究应进行更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分析,去阐明真实的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社会关系、权力动态和思想如何应对这种反应。最后,博尔琛提出了问题: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历史脉络下,气候史研究者应如何将社会和文化的两种价值纳入其中?

竺可桢,中国历史气候学的奠基人
郭庆分享了fiona williamson的the “culture turn” of climate history: an emerging field for studi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一文。该文主要关注气候史的“文化转向”在东亚的发展与应用。东亚变化多端的气候为东亚气候史的“文化转向”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东亚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仪器和天气记录的基础上,以竺可桢为代表的学者们发展出了丰富的历史气候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历史气候资料的收集与重建、将重大事件与气候联系起来以及极端天气对社会变化的影响等问题上。此外,由于这些定量研究局限于自然档案,倾向于将气候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化,因此有时候甚至会倒向“气候决定论”。因此,气候史研究应多关注社会档案,并引入人文学科的方法与视角。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充实关于气候影响社会的背景信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和动态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弹性而非机械响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这些研究挑战了原有的气候导致饥荒、战争等结论,通过个案揭示气候变化在历史上的隐藏作用,将历史叙事和气候重建结合,并进一步探索社会视角下的气候。沿着这条路径前进,文化转向便提倡从文化上理解气候并丰富气候的概念,探索气候与社会文化和大众信仰体系的相互联系。fiona通过两个案例进一步介绍文化如何理解气候以及两种档案是如何结合的:沿海地区的台风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气候文化,这成为外国和本土观察者对地方和文化叙事组合的关键部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盛行的祈雨显示出文化当中对气候的认识。这两个案例说明对气候的“社会记忆”在处理、解释和管理流行文化和传统社会的天气方面有着强大的应用。fiona最后指出,现实世界的紧迫要求我们进行“文化转向”,并提倡更全面的气候史研究和更大范围的综合研究。
除此之外,领读人还对文章的目标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文章的对话人及其学术倾向。在最后,领读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如何界定自然档案与社会档案?在气候史研究中,气候文化史与气候重建的关系是什么?气候文化史应该居于什么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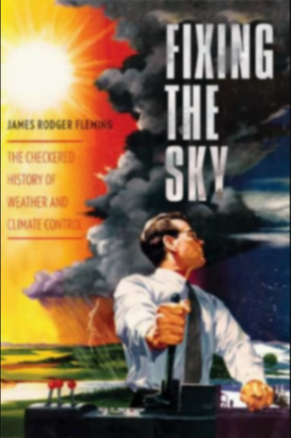
美国科尔比学院科技史学者james r. fleming的著作——《修复天空》( 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仇振武以《世界历史上的厄尔尼诺》一书为楔子开启了对james r. fleming的climate, change, history一文的领读。仇振武介绍和分析了fleming的生平及其具有跨学科特质的科研历程,并对其《修复天空》(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2010)等著作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以此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治学路径与学术观点。仇振武分析道,fleming在该文中首先对气候的概念以及气候学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他认为气候不单单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与经济、种族、历史等议题联系密切,尤其强调气候与历史的关系。在fleming看来,气候史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年代气候学,年鉴学派以及作为科技史的子领域。然而,fleming对气候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并批判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气候史“不是狭隘的个案研究或宏大叙事,而是具有重大意义、广阔视野和悠久历史的‘全景历史’(big picture histories);不是所有环境和历史,而是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大气环境”。很显然,fleming理解的气候史既不隶属于科学史,也与环境史有所区别,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
作为最后一位领读者,仇振武对三篇文章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了简单总结。例如,在什么是气候史方面,fleming和fiona都强调了“气候史”与“历史气候学”的区别;在气候史的文化转向方面,三位学者都持肯定态度,但在地理空间上,fiona强调了气候史的“亚洲转向”;在对环境史的态度上,fleming似乎颇有微词,fiona则积极肯定了环境史的贡献;而在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忧虑下研究气候史,则是所有相关学者的共识。此外,仇振武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有必要区分“历史气候学”和“气候史”;应承认和借鉴环境史、科学史等学科对气候史、气象史的作用,其中环境思想史也契合了气候史、气象史的“文化转向”;对地方知识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出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张力;气象史的学术发展脉络与气候史也有所不同。
随后,与谈嘉宾对三位领读人的分享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敖友华首先分析了第一篇文章的背景、方法以及观点等内容,认为该文作者对拉丁美洲方面的介绍非常充分,提及了许多气候史以及环境史的术语,对气候史的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介绍,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其次,他也指出文章值得改进之处,诸如在中国方面涉及较少,在一些问题上处理过于简单等,并对领读人能在讲解中对论文的一些内容进行补充表示赞赏。同时,敖友华也指出了一些可以研究的方法,并且想知道文中的哪些方面与领读人的研究有关。在对郭庆的领读进行评议时,敖友华表示了解东亚的气候特征至关重要,但目前研究更多地关注海洋,其实内陆的气候问题也值得关注。作为学者,应该注意气候史中自然和人类因素的相互关联,在研究上可以将社会变化与气候历史联系起来,同时考察历史上的概念、观念和习俗。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思考,例如如何使用不同的档案,如何选择合适的分析框架,等等。敖友华认为,第三篇文章更像是一篇总结性的论文,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是让人们知道气候的文化史很重要,并且激励未来的研究人员。但是作者对气候这个词的解释是从西方历史视角出发的,实际上东亚与中国的气候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图景,不同地区的气候观念受到各自文化的影响。敖友华对仇振武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气候史应该是环境史的子集;由于天气、气候等术语与概念的紧密联系,气候文化史也可以看作思想史或者科学史,一般情况下无需进行严格的区分。
乔瑜指出,关于气候等自然知识的生产具有不确定性,气候史研究的意义重大,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批判和补充,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突破。气候史因此成为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其关注到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共同演变,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她认为,气候史研究也有内外史之分,气候外史研究给职业历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使其能够补充气候内史研究,弥合了合理性和现实性之间的间隙。对于论文中涉及的话题,乔瑜还讲述了自己关于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气候史的研究,该研究探索了传统气象学知识科学化的过程,她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经济如何影响气象学科的发展。
孙萌萌引用了mike hulme的文章climate and its changes: a cultural appraisal对博尔琛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补充与回答。她认为,气候让人类在文化中与天气相处,其为人们本应过于混乱和令人困扰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天气经历引入了一种稳定或正常的感觉。因此,气候和文化是一对二元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气候和文化之间的二元沟通也就成为理解气候或文化概念的必要部分。孙萌萌以dagmar schäfer(薛凤)教授等的what is local knowledg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yuan dynasty disasters in imperial china's local gazetteers一文为例,解答了关于自然档案与社会档案区分的问题。她指出,从自然档案到社会档案的转变不在于档案的类型与内容,而在于观察和解读的视角。比如在这篇关于地方志的研究论文中,灾害记录不被视为真实发生的事件,而是被视为一种话语,是一种认识论实践的地方知识的表现。她认为,这种视角转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灾害的政治性和文化性,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于自然因素。对于气候文化史与气候重建的关系,孙萌萌认为,气候的文化转向代表着范式的转移与视角的转变,其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将完全不一样。而这之间的视角、问题和哲学基础都不同,因此两者之间很难融合。
在小组讨论环节,几位领读人首先对评议人的发言人进行了回应。博尔琛认为,该文涉及气候史的广泛领域,但也有过时之处,因此他引用了一些后来出版的书籍进行补充。该文给他带来了研究方向上的启示,使他进一步思考气候史研究文化转向的意义。郭庆从切身体验谈起,认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气候的体验,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充分的表达。对于气候重建与气候文化史之间的通约问题,他也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一些思考,认为需要更多的人文学者投入到气候史的研究当中。仇振武肯定了乔瑜关于传统气象学知识科学化的思考,认为气候史、气象史本身的特质为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打开了窗口,成为值得深入探索的跨学科领域。
随后,与会者对如何引用气候重建以及自然科学家利用历史档案所进行的工作进行了自由地探讨。仇振武在回应关于地方志的问题时说道,历史研究的不同尺度和能见度,影响着我们对气候与历史关系的看法。在大尺度上,气候与社会的紧密性更加显著,但在小尺度上,就更加微观与细致的研究而言,或许气候的因素就不那么重要。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尺度的处理,deborah coen的climate in motion一书值得参考。敖友华认为,当我们依赖于社会文献进行研究时,气候重建可以帮助检查我们关于特定事件的研究,从而得到社会档案和自然气候历史的综合,但对于这种综合问题的探讨仍然是相当棘手的。孙萌萌认为,自然档案及社会档案的结合本质上是两种视角的结合,在气候重建基础上进行文化与历史视角分析或许会遇到一些困难。郭庆认为气候重建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一种错置,人们对气候的实际感受与气候变化趋势并非必然一致,由于气候重建的分辨率问题,在分析小尺度问题时这种错置会大量存在。乔瑜最后进行总结:大尺度上气候重建工作是有共识的,这是人文学者得以研究的重要基础。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拼图,而错置提供了这种拼图的线索。气候的重建和历史的重建是在两条不同轨道上对于世界的描绘,彼此之间互有影响。
最后,观众向孙萌萌和敖友华提出了关于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以及如何将西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的问题。孙萌萌认为,数字人文给定性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定量的分析方法,两者在尺度上也有大尺度和微观分析的区别,如果能够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将会推进问题分析的深度。她为此推荐了一些使用相关方法的文章。敖友华认为,西方与中国的气候文化既有差异,也有共通之处。例如,挪威和中国都有一种民俗,就是根据特定时期的日照情况,来预测未来一年的气候变化。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通力合作。
领读文献:
1. carey, mark. "climate and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ical climat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historiography."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3.3 (2012): 233-249.
2. williamson, fiona. "the “cultural turn” of climate history: an emerging field for studi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11.3 (2020): e635.
3. fleming, james. "climate, change, history."environment and history20.4 (2014): 577-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