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醒龙、黄建新谈文学与电影领域的现实主义表达

1990年代初,黄建新意识到市场电影和艺术电影是有区别的。只有让中国电影大规模化发展,让更活跃的人去推动电影市场,才是良性的状态。在此之后,他拍摄了电影《站直啰,别趴下》。图为《站直啰,别趴下》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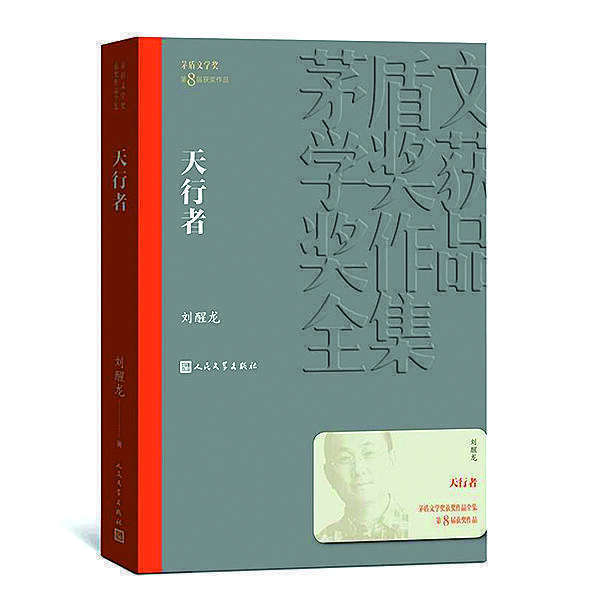
《天行者》刘醒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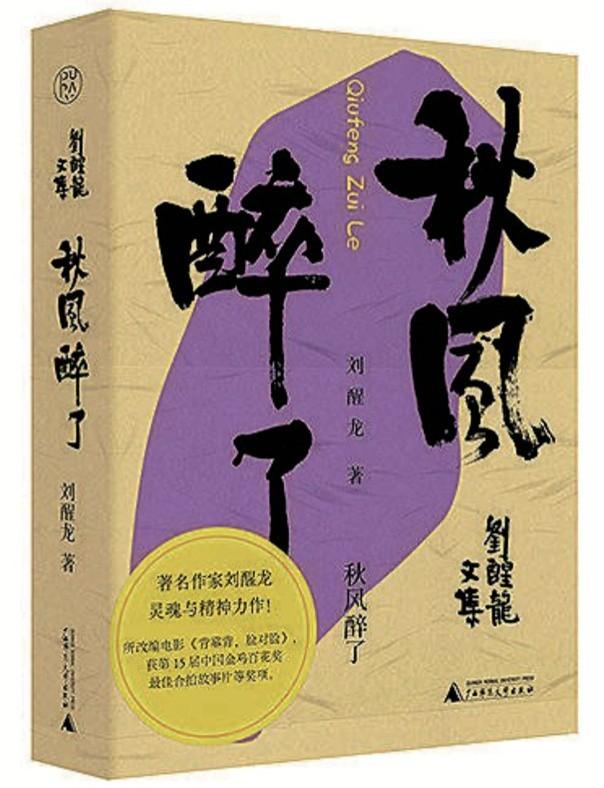
《秋风醉了》刘醒龙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影与文学,都是研究现实与人生的艺术。如何以现实为基底进行艺术创作,如何塑造让人共鸣的艺术形象,如何平衡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是电影和文学共同探索的问题。所以,不管在小说还是电影领域,“现实主义”都不是新鲜话题,甚至是老生常谈。但如何能真正做好“现实主义”,又一直是创作者面临的“难题”。中国电影需要现实主义,所以会向小说“借力”,但中国电影市场还需要观众与票房,需要新的美学形式。这三者本不矛盾,若处理不好,则会呈现出一种割裂性,这在当下电影中也屡见不鲜。
不久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期巅峰对谈活动中,著名导演黄建新与著名作家刘醒龙就此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小说与电影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边界与维度。
本报获得授权,对此次对谈进行独家整理与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嘉宾:黄建新 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金鸡奖最佳导演
刘醒龙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主持:刘小磊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现实与虚构之间——从小说到电影
刘小磊:《背靠背,脸对脸》是改编自刘醒龙老师在199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秋风醉了》。《秋风醉了》和《菩提醉了》《清流醉了》一同构成了您的文化馆系列小说。小说故事生动得几乎像现实搬演。您认为小说和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刘醒龙:在文学界有一个行话,对现实主义品格的文学作品称之为“正面强攻”。这是一个军事上的术语,军事“正面强攻”是最难的。在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是最难的。我们对于现实很熟悉,但实际上未必人人都能理解。小说和现实的关系,我觉得首先是精神和灵魂的一种交流。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我们自然了解现实,理解现实,甚至我们就是自己创造现实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呢?就是因为人和现实之间还是需要有一种东西进行沟通,这个东西包括小说、诗歌、散文,也包括电影。
刘小磊:黄建新导演最初是怎么发现这部小说的?您从《黑炮事件》开始,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作品在诙谐呈现的同时,都有着直面现实的力量。您选择小说进行改编的标准是什么?
黄建新:这部小说是在宁夏的时候,我正在拍《五魁》,有一天我的联合导演杨亚洲在现场拿了一本《小说月报》给我,让我看另外一部小说。我看了,写得很好,但是没有让我那么着迷,我就往后翻,紧接着就是《秋风醉了》。我大概看了三分之一,就说“亚洲,赶紧找,这个在哪里”。看的时候我有特别多的联想,有感触,这是最直接的。
我自己拍的电影大量都来源于小说。因为我大学是中文系的,喜欢看小说。小说比电影带来更多的联想空间。电影只提供一个具象的东西,观众总会顺着你营造的事物走,而消除了自己的空间联想。同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联想,你的电影能不能说服观众就很重要。所以电影的二度创作能否把有深度的小说转化为真正具有魅力的电影作品,是很有挑战性的。
电影史上比较好的电影其实大都来自小说。作家不同于导演和编剧,因为编剧创作剧本几乎不能完全进入个人的创作状态,会有很多外部条件的干预,而作家不同。小说能提供更丰富的东西,这是电影的精神源泉。
刘小磊:醒龙老师很擅长写中国式的人际交往,各式各样的圆滑处事非常有经验,或柔或刚,弦外之音,都处理得有声有色,而且小人物的性格鲜明,像王副馆长、老马、小闫等等。这种生动的人物处理方式,在经验和虚构之间,您是怎么处理的?您在观察和塑造人物方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创作经验?
刘醒龙:我的小说中一向有一种自己风格的坚持。大家在关注作品时往往最关注主要人物,就像《秋风醉了》里面的王副馆长,忽略了次要人物。而我的小说里,次要人物写得好不好关乎作品的成败。你跟着主要人物走不大可能失误,失误的、有缺陷的往往是次要人物。一个作品的魅力也是次要人物烘托起来的。小说写作领域里面有一句行话“小说的艺术就是闲笔的艺术”,看你闲笔写得好不好。好的闲笔砍掉了,作品的光芒光辉、风格风采就消失了,这就是好的闲笔。小说的闲笔,决定这个作品的高下。我一直最努力写的是小说里的次要人物,甚至是特别次要的人物。有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让这个作品有血有肉,否则就是骨架。
刘小磊:还想聊一下您笔下的父亲形象。您曾经刻画了非常多的父亲形象,大多勤劳朴实、隐忍节俭,他们也会有一些劣根性,但也能被读者理解。像《秋风醉了》里的王双立的父亲,虽然一心想要孙子,但是真听说儿媳妇怀孕了,他要回乡养猪给娘俩儿补身子用。面对小闫拿来的高级皮鞋,他确实不知怎么的,没用力鞋子就破了,他还因此痛心和自责。您对于父亲、父辈的描述,基于怎样的态度和现实考量?
刘醒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文化界,甚至是整个的文化界,弥漫着“审父情结”,就是对父辈的批判和重新审视。这是从西方哲学引进来的。我也有过。在我的内心,像《大别山之谜》这种先锋色彩的作品里面,父辈的形象确实不是很好,对父辈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写作风格就慢慢调整过来了。
刘小磊:但黄导在改编后,父亲形象会变得更加尖刻和厉害。他看似沉默,主动帮人修鞋,也能够隐忍。但实际他是有自己的狡黠和心机的。他想惩罚小闫,所以借机戳破了皮鞋,大闹之后到医院卖血。这让电影的尖锐性变得更强了,也让电影显得更具有城市性的特征。您是如何理解1990年代的父辈形象的?在当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您是怎么处理那种讽刺性和批判性的?
黄建新:其实我想表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对立状态,比如《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都是讲这样的一种状态。《背靠背,脸对脸》中,局长一直不让王双立当馆长,但是一退休,那个局长是个非常可爱的老人。有的时候,人的好坏,不是简单的权力利益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三部故事,都是以群像为主体的。这个就特别逼近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生活经常是这样的,各个层次、各个年龄、男女老少,构成了我们生活所沉浸的一个圈。这三部电影就是想表达这种沉浸。
其实涉猎到心理层面上的意识,有一种叫“集体无意识”。我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表现存在在心理上的问题,能够警醒我们。人变得单纯,是一个最难的事,但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人能够透亮、欢快、单纯。可其实,司空见惯,甚至不以为然的事情,往往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就是当时处理父亲那个人物时大概的想法。进一步讲,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是极为微妙的,一生也弄不明白,但想躲又躲不了,这就是现实。所以,每个人都希望用坚定的毅力和追求来保持自己完整的人性,这也构成了中国人生命的特点。
转型与创新之间——现实主义的当下性
刘小磊:两位老师在1990年代都有过一次重要的创作转型。醒龙老师现在是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但最开始您在1980年代创作《大别山之谜》时,是非常先锋的风格。您是怎么从当时最时髦的先锋文学创作,转向了对现实的关注?
刘醒龙:有很多契机,但最重要的还是人生的阅历和写作的体验,以及个人在艺术修养上的慢慢积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孩子最不喜欢谁?是父母,他们是最爱你的人,最心疼你的人,给了你生命,但你最不喜欢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给你责任,跟你唠叨,批评你。文学也是这样。现实主义就像父母,你特别了解他,就一点儿神秘性都没有。但像其他风格,魔幻的、先锋的,很容易玩出技巧来,那个东西就特别吸引人。但慢慢的,你会发现,现实主义是人生的主流,也是艺术的主流,也正是因为如此,主流就最容易被忽略。后来当我认识到现实主义是最重要的品格时,就认准了这条路,一直走下来。
刘小磊:黄导其实也是如此。《黑炮事件》到《错位》《轮回》都是比较先锋的创作风格,但到了《站直啰,别趴下》,视听锋芒感消失了,情节处理也更偏向温和和喜剧的现实主义创作表达。为什么做了这样改变?
黄建新:1980年代,不光是电影,小说、绘画、诗歌、戏剧等,都开始出现新浪潮。在学校,同学们都读尼采、弗洛伊德,似乎我们可以看全世界,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看,探索各种艺术形式的可能性。标新立异就是当时最冲动的想法,所以《黑炮事件》《错位》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中国电影票房一年只有不到八亿了,电影没人看了。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都需要借钱发工资,那是电影特别低迷的时期。
我们在学校念书时,学校教给我们“电影是大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这对我是有影响的。1990年代初,我去澳大利亚做了一年多的访问学者,去参加电影节,我意识到市场电影和艺术电影是有区别的。我们要让中国电影有大的规模化发展,有更活跃的人去推动电影市场,这才更需要探索,只有这样,才是良性的状态。从澳大利亚回来后,我就拍了《站直啰,别趴下》。
刘小磊:醒龙老师是非常勤奋的作家,尤其在2000年后,从自己擅长的中短篇领域,开始往长篇小说进军,像《天行者》《圣天门口》都取得了非常高的荣誉和肯定。请问保持这种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是什么?当生活的一切变得更加稳定后,创作思路会逐渐固定和局限吗?
刘醒龙:从2000年到现在,世界变化之巨大,不可思议。但是,在不可思议当中,我还是对人本身表示坚定的信心。必须对人自身有信心,才能获得幸福感。人和万物不一样,就在于人是彻底的感情动物,是彻底的抽象动物。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易变。包括ai,我不相信ai能统治世界,ai在艺术领域永远比不上人。人的感情需求太复杂了,真的说不清楚。就像写小说,1990年代末,突然之间长篇不流行了,没人看了,出版社印的书卖不出去,不允许超过12万字。人家说我的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不写了,为什么不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写中篇和短篇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不存在任何挑战性。生命有限,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们这一行做什么呢?于是我写长篇,《圣天门口》写了六年。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读者,文学创作,作者写完最后一个字只是完成一半,接下来在印刷出版和传播过程中是读者说了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读者就这个水平,读者总是希望自己更进一步的。我觉得电影也是这样。
刘小磊:现在创作群体是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的,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作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前辈,你们认为现在搞创作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处理所面对的现实瓶颈和虚构之间的关系呢?
刘醒龙:我绝对相信年轻人的艺术才华,但是会对他们的生活经验打个问号。我们在艺术创作上最大的瓶颈,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还是阅历。这个阅历不是说在机关里、在单位里的那种日子,那只是很小的一面。有一句话叫“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未来的艺术家、未来的文学家需要的是非常慎重地去看待世界。
2021年的时候,我坐一艘渔船,随着海南水上考古队在南海待了半个月。四平方米的船舱里面睡两个大男人,那也是对心理极限的一种挑战。有一个小岛叫“全富岛”,我们前一天下午去那个岛上的时候,岛上还是光秃秃的。很小很小的岛,全是沙滩。那个海滩生成的时间不到一百年,有记载的。我们第二天早上上那个岛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岛的中间有一个植物长起来了,很神奇的,它就是让我们去见证。我们一定要作为生活的见证者,首先作为广阔生活的见证者。我们一定不能离开生活,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什么生活?我们不能离开广大的社会生活,只有广大的社会生活非常丰富的时候,才能让你的作品丰富起来,从而变成伟大的作品。
黄建新: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就是因为年轻,敢做敢冲,敢不按说的办。当年我拍《黑炮事件》,那个大钟表四分钟不动的镜头,让我重拍。我给西影厂的厂长吴天明打电话,他也正在外面拍戏。我说“我不想(重)拍”。他说“你确定你是真的有想法,不是照猫画虎?”我说“我是一个体系,我确定有想法”。这就是年轻人。因此,指导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挺难的。因为是年轻人生活在当下,对当下生活的理解,年轻人比我们敏感。每一代都在变,这个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否则时代就不前进了。看现在年轻人的语言,你会看到他们对喜剧的理解,对语言幽默感的理解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变化,是语境的变化,是语境的变化带来所有的变化,包括艺术也会变。这其实是年轻的优势,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和现在年轻人不同的是,当年我们都经历了特别多生活中的事。比如醒龙老师,他在文化馆经历了很多的事,我们这代人都下过乡,当过兵,经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这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具备的,所以希望大家把视野打开,多读一些社科类的书,读一些哲学的书,这对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能够比较洞彻地认识世界和分析事情是有好处的。我自己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当时觉得好多书读不懂,没啥用,但是很多年之后,遇到某件事情,突然把书翻出来再看,觉得非常有用。仅此而已。年轻人,大家努力往前冲就是了!